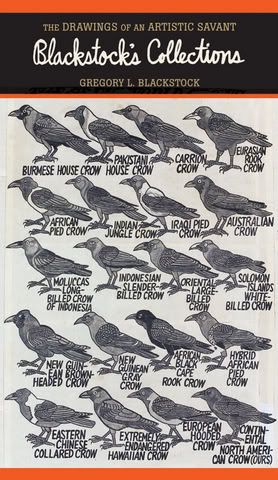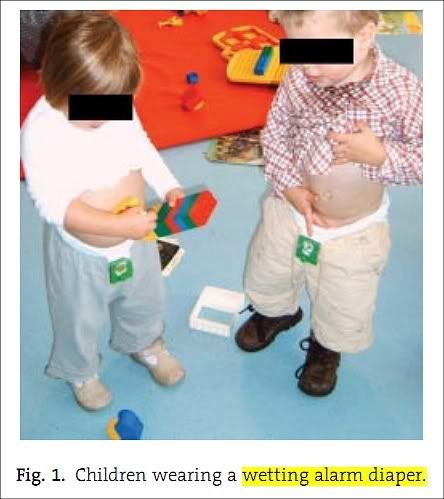實在不怎麼建議上台北縣環保局網站,因為太吵了,每次換頁,所謂的環保影音(事實上是東森新聞)就要重播一次。我是為了要去抓一張交通工具碳足跡的計算表格,忍人所不能忍。
就是下面這張。其實,很多網站都可以算碳足跡,也是說看你一天做了些什麼事-吃喝拉撒,用掉多少能源,排放多少溫室氣體。這張表比較簡單,它彙整了所有交通工具一個人坐一公里或搭一次會產生多少二氧化碳。

然後呢?我只知道一個人騎機車一公里跟坐火車一公里排放相同的二氧化碳,但你相信嗎?更怪的是公車排放二氧化碳量竟然是用搭公車的錢算的。當然,這東西要簡化、生活化我沒意見,誤導或迷惑大家就不太好了。
你都不會想知道從自己家去到公司,開車、坐公車或坐捷運哪一種排放二氧化碳量少?請問,從上表怎麼比較?也許你會。
好了,就不要管上面那個表格了,忘了它。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如果我開車到公司上班,從車子發動到到達公司,這一路排放出來的二氧化碳都是我負責沒問題;如果是坐公車呢?當然是同車的人要一起分攤。同車的人多,我分到的就少;同車的人少,我分到真的會比自己開車少嗎?
你說坐捷運最好,那我就想,我自己開車的時候會把整個地下鐵道的空調、電燈全部打開嗎?這些難到不需要算到捷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裡?
總而言之,溫室氣體只算交通工具運行時的排放是不夠全面的,要算整個生命週期的排放下去平均才會準確。
以火車來講,如果真的要算就要從火車的製造、車站建造、鐵軌鋪設、電力系統架設、電力生產、柴油煉製、設備維修、燈光、空調、清潔算起,到火車啟動、行駛、怠速、停車等等,假設一台火車 50 年壽終正寢,把五十年這一切二氧化碳排放都加起來,平均算到一個突然去搭火車的路人甲身上,這才合理。
這叫做歷史共業。
沒有什麼不可能,底下這幾張圖表就是這樣算出來的。

表上的交通工具依序是轎車、休旅車、小貨車、柴油公車(離峰時間)、柴油公車(尖峰時間)、三種捷運、小、中、大飛機。
從上表可以看得很清楚,白色斜線的部份是每一種交通工具運行時的里程人均耗能、排放量,整個柱狀則是生命週期的里程人均耗能、排放量。
其實我們最需要的不是在那裡算今天排放了多少二氧化碳,而是需要像這樣的圖表,有個清晰的概念知道自己怎麼做比較好,或是知道政府最好不要做什麼。
如果你看到離、尖峰時間的公車排放量差距,你就會了解擠公車是多麼愛護地球的表現。如果你也看到捷運興建的環境成本,大概也就不會太讚嘆捷運運行時排放那麼少的溫室氣體了。
圖表來源: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of passenger transportation should include infrastructure and supply chains. Doi: 10.1088/1748-9326/4/2/024008